动物属于科学吗,动物学科
今天这本书《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有意思了,说的是中国古人如何认识和看待动物,动物又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伦理道德,以及审美观念,产生过哪些影响。
本书的作者是英国汉学家胡司德,他是剑桥大学客座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中国史学的新代表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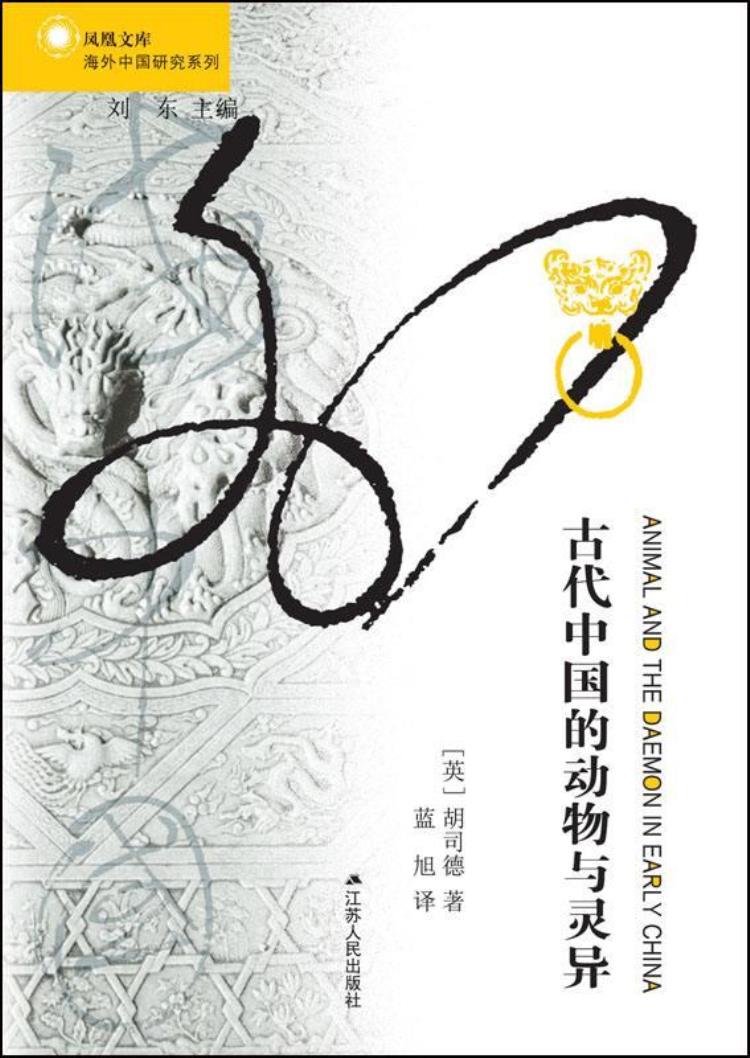
说起胡司德这本书的缘起,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他还在剑桥读研,偶然读到了一些资料,就是李约瑟那套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相关笔记和档案——那可是一套七卷三十四册的巨著啊,换算成中文,少说也有3000万字,然而胡司德发现,这么一套煌煌巨著里边,关于中国动物学的内容,少得有点不成比例,而且从李约瑟参考的文献来看,他好像也没有在这方面太下功夫。这就让胡司德感觉,发现新大陆了。他决定研究这个课题,并且,他选的研究路径很独特,不是从生物学意义,而是从文化意义上来研究。终于,通过阅读海量的中国古文献(光是书后的参考文献名录就列了70页),他写出了这本《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

先看中国古人对动物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人可以说是漫不经心。胡司德通过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发现,天文、医学、历法、占卜这些方面的文献很丰富,而同时期与动物有关的文本实在是少而又少。
这个情况,再横向对比一下就更明显,跟战国同时代的古希腊,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动物学研究资料,跟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已经有老普林尼的《博物志》这样37卷本的自然百科全书。这么一比较,中国文献里关于动物的资料,就显得太匮乏了。
不光是资料少。中国古代文献对于动物的定义也相当浮皮潦草。比如,基本的分类就只有“禽”和“兽”这两大分枝,成书于汉代的《说文解字》,对禽兽的区别是这样解释的:“两足为禽,四足为兽”——这简直是对付事儿;反倒是成书更早的《尔雅》稍微认真点,说“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但同时还搞出一堆含糊不清的分类,比如,“鳞”就是指有鳞的动物,“介”就是指有甲壳的动物等等。但究竟是指什么动物,也没交代清,搞得后来的学者们争吵不休。

这种对动物分类学的不重视,让不少汉学家都感到很困惑,甚至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就是《朱雀》的作者,他就曾经断言,古代中国就没有生物学、生态学的概念。
那么事实如何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汉学家看中国的眼光太“西方”了。如果说符合西方,或者现代定义的动物学,那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不过这不是中国古人缺少观察力,也不是对大自然没兴趣。比如,孔子就曾经让学生们多学习《诗经》,说不仅可以培养好的品质,还可以多识别“鸟兽草木之名”。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明确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就是说,《诗经》里关于自然万物,乃至动物的雌雄之别,都有记载。
这样来看,古代中国的学者们不是没注意到给动物定义、分类的问题,而是有意忽略了从动物学角度,而更倾向于把动物的定义拔高到了社会学层面。中国古人和西方人对动物的关注点不同。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胡司德认为,这是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造成的。主观上说,中国古人习惯于从文化意义上去理解动物,假如把动物物种定得太细,不同动物物种的品性、特征什么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你就没法为动物赋予某种意义,来传达你的理念了。另外从客观上说,中国古代的学者,以教化人、建立稳定的社会体制为终极目标,也不一定有剩余的精力去搞动物研究,再说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研究条件。
受制于这些主客观的因素,战国、秦汉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动物的了解很匮乏,更要命的是呢,他们有时甚至还以这种无知为荣,觉得这是自己心无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体现。比如汉代著名的政治家,大儒董仲舒,他写过一本书叫《春秋繁露》。书里说自己因为勤奋治学,“三年不窥园,乘马不知牝牡”,连公马母马都分不出来,而在他看来,这还是件挺值得夸耀的事儿。

当然可能你会觉得不对,比如“伯乐”,他不就是因为精通相马而出名,并且受人尊重的吗?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伯乐”,他原本是春秋时候秦国的相马师,本名叫孙阳,擅长鉴别马的优劣,人们说他简直是掌管天马的星宿伯乐。一来二去,就用“伯乐”来称呼他了。后世把有识人之明的人叫作伯乐。不过伯乐的传说得以流传,不是因为后世推崇他鉴定马的技术,而是因为伯乐这个形象寄托了文人的一种理想:“学会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希望有伯乐这样的人来发掘、举荐自己,所以说,伯乐的盛名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动物学意义上的。
由此我们就能发现,中国古代对于动物漫不经心的定义,导致了动物在中国文化里脱离了它们本来的生物属性,而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进而在社会秩序和权力体系里发挥作用。那么,动物们是怎么在中国古代体制中出场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动物,与中国古代礼制观念和社会等级的产生。

在这我们要先探讨一下,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么这个“礼”,它最初的含义是什么?简单说,“礼”体现的是一种秩序,它要求人,乃至万物,都处在自己最适当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既是指地理位置,也指社会地位。古人认为,这种“各就各位”的状态,就是最理想的,代表着平衡、守序。
那么这个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国最古老的一本书《尚书》,其中的《禹贡》篇记载,大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划分为九州,那么这九州是根据什么划定的呢?作者提出一种可能,就是,以各地不同的物产为依据。后来的《逸周书•职方》就列出了各州的动物名单并标注上“其畜宜”,就是说这个地方适宜这些动物生存。《周礼》《汉书•地理志》的描述也差不多。作者解释说,这可能就是参考了动物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动物都有自己大致的活动范围,而中国古人主要的活动地区,就是所谓中原地带,气候差不多,也没有非洲那种季节性的动物大迁徙,所以在古人眼中,动物都是安守着自己的栖息地,不会越界。并且进而认为,这是一种我们应当遵循的、自然界的规范。

古人观察到这一点,就也开始效仿,比如前面提到的《周礼》,里边就规定不同地区的军队使用的旗帜、符节,都要跟他们这个地方的物产属性相符。比如多山地带用虎节(就是老虎形状的兵符),多水地带用龙节,等等,《管子•兵法》对于军队徽章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既是为了辨识,也有辟邪、祈祷的意思。
后来,这种认为人和物都应当待在自己的领地上不越界的观念,引申出了新的含义,就是强调人要安守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同社会等级,从身份、职业到待遇,都是不同的,有严格界限,而且这个界限是不可逾越的。这个就是“礼”。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春秋时候郑国有一位著名的大臣叫子产,《论语》里有提到过,孔子对他评价还挺高。这位子产就说过,根据礼制的规定,只有君王可以享用“鲜”。这不是说只有君王才能吃新鲜的食品,“鲜”是指野外捕获的动物。这就是把自然界的食物链关系,对应到人类社会里了,就像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可以吃任何其他动物一样,对野生动物的使用权,也是王的一种特权象征。

从这就能看出,虽然“礼”要求人和动物都不能越界,但是,处在“礼制秩序”顶端的君王可以。历代君王们通常都会有苑囿,在里边养上来自各地的珍禽异兽。文献上也经常能看见边疆地区或者外国进献狮子大象之类中国没有的动物,君王们总是很乐意笑纳。这不是因为他们爱动物,而是因为,他拥有了一个地方的独特物产,就象征着那个地方对他的臣服。就这样,动物,被视为王权扩张的象征。
最有名的皇家苑囿,大概要数汉武帝的上林苑,司马相如写过一篇著名的《上林赋》来描述它。而汉武帝著名的“汗血马战争”,背后也是这个逻辑。为什么他要不惜代价发动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进攻远在西域的大宛国,真的就为了几匹马吗?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汉武帝当时正在全力向西域扩张,而他的上林苑里没有汗血马,就意味着汗血马的产地大宛没有向他臣服,所以必须获得汗血马,以此来向其他西域各国证明,他在这的最高权威。

今天先到这里,明天继续。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喜欢我的文章就果断关注转发吧。







